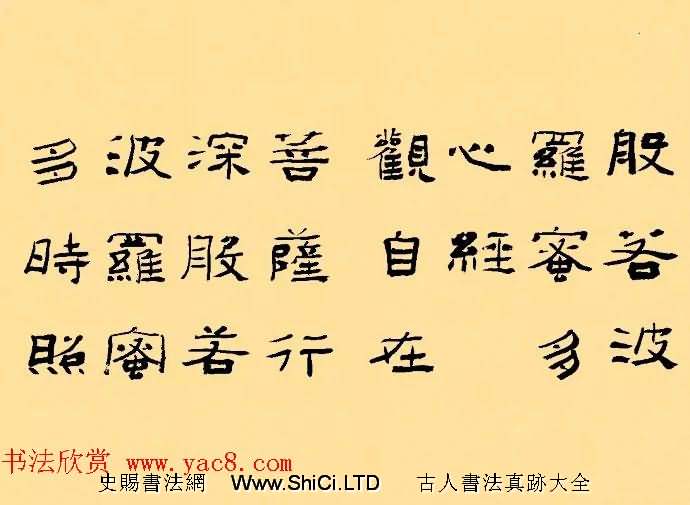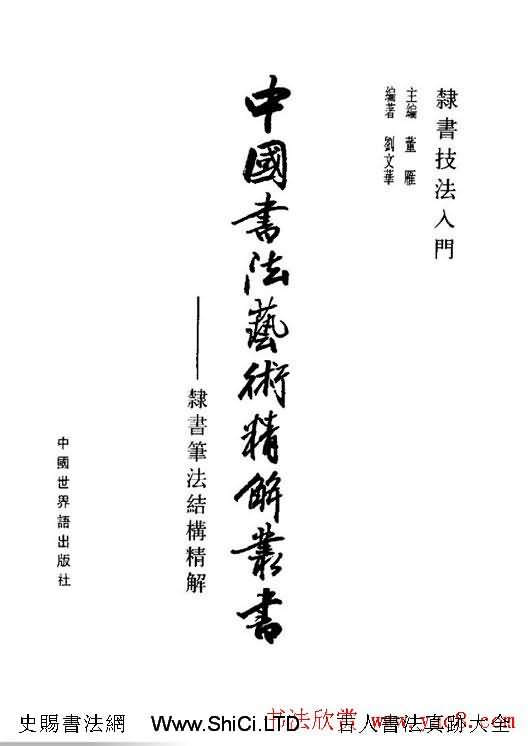一、臨帖是在臨什麼
臨帖是每一個學書法者不可缺的功課,如何臨帖是學書者都想急於解決的問題,而劉文華老師認為,在此之前,首先要弄明白臨帖是在臨什麼。他說,我們入門學古人的時候,就是把古人的規矩擺在了桌面上,臨帖就是學規矩,而不是別的。在臨帖中你要弄點輕重、虛實、濃淡、正欹出來,這些都是微觀變化,是情緒化的東西,而宏觀的東西不能沒有,這是關鍵,否則就沒有從理上去處理它,讓人一看就不合規矩。因此外形的東西從理,也就是說,字的外形、結構、筆畫的位置等從理,從字理,即中國漢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規則和法度;而筆則從書,反映的是趣和味。這是兩個原則。外部形態的東西是一目瞭然的,合不合規矩一看便知;用筆則是書法本體的東西,粗細,放收,快慢,墨的濃淡,都是書法本身要求,決定字的味道,就如我們吃的各種菜系,魯菜,川菜,粵菜,用筆不同決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結構是理性要求,是中國漢字的形體美要求,必須嚴謹,無論行書還是隸書,這是書法的基礎,這是兩個不同的原則,臨帖就是在學習這種理法和原則。
二、目前的訓練你要幹什麼
知道臨帖要臨什麼後,接下來就是如何去臨。訓練就是解決如何臨的問題,因各人喜好不同,對所臨帖子選擇不同,但是,無論哪種帖子,拿來後你不管如何取捨,訓練時要針對你所取的東西,形成一種科學的訓練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覆實驗、繼承與鞏固。在講評學員的隸書時說,筆畫不能單一化,簡單化,不能單薄乾枯,要立體圓潤生動,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筆畫無數種不同寫法,加以對比模仿融合提煉,在對比中找出共性與個性,找出同一筆畫的不同形態與表現手法。創作時把碑上的字形拿過來,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現,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創作中手法決定風格,手法變了風格也就變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我們現在示範的只是一般的,不同的碑其手法不一樣,張遷、鮮於潢相類是一種,禮器是一種,而曹全又是一種,你如果能把這些碑的手法都掌握,創作時把它們用於同一張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訓練時我們就要像這樣有目的的去一個個的解決問題,那麼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沒人能追得上你,因為你一直走在前邊,把問題都解決了,而這些問題有的人恐怕一輩子也想不到,所以他只能做個愛好者。因此,訓練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進行取捨。要想比別人取得更大的成績,並不是說你要比別人加多少倍的勁、花多少倍的錢、用多少倍的時間就行,你必須有不同於別人的思想,在這種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選一個不同於別人的方法,確定一個科學的訓練模式,然後你才會有不同於別人的結果。也就是在用腦子寫字而不是用手。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分析自己的癥結所在,頭痛治頭,但如果是由腳氣引起的頭痛,就應先把腳氣治好,對症下藥,比如說你們學草書的,應該先學行書,通過行書練技法,使轉、提按、收放、筆畫之間呼應、上下字的連帶關係等等,練好之後,草書就只是個草法問題了。我們教書二十多年,基本上都用這個方法,草書嚴格講不是學來的,因為從它生成的原始狀態看就是一種極度情緒化的東西,由行書提練字形、用筆和手法,是一條正路,這是個方法問題。你現在在臨《書譜》,對於《書譜》,你要明白,首先是學他的文章,其次是學他的草法,再次學他的字,在臨習時要挑字臨而不要統篇抄,嚴格上說《書譜》只能借鑒而不能學,縱觀二十多年來,靠書譜出來的就一個倫傑賢,但倫傑賢先是學得米芾,寫米寫絕了,因此他是把創作落在《書譜》上而他的功夫卻是下在米芾上。寫《書譜》寫了一輩子的孫墨佛怎麼樣!你像現在的有些中青年臨書譜有成就的,他們都是在借鑒書譜,巧用書譜而不是實寫,因此,訓練思路要對。
三、寫字不在於多而在於對,不在於法而在於理,要過單字關,不能只抄帖。
講評學生的行書臨作時,劉文華老師一邊示範一邊講到,行書的技法是上一筆管著下一筆,下一筆接著上一筆,你的寫法是這個不管那個,那個不管這個。行書的上一筆是下一筆的起筆,下一筆是上一筆的收筆,行書在筆畫上已經把楷書一筆一畫的概念破壞了,可能是三個或五個筆畫變成了一個筆畫,每一個筆畫之間都有內在的聯繫,相互管著,因此,寫字不在於多而在於對,不在於法而在於理,你寫得行書理不對,法上才出了問題。草書更是如此,比如這幅《書譜》的臨作,他的臨帖的思路、觀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練,學草書時要注意草法,特別是一些典型符號的練習,一定要強化練習,專門練習,一個符號半個小時應能解決、吃透,能用後半生,何樂而不為,但書寫時要注意變得自然而不是疆硬。
還有一個現象,臨帖者往往追求數量,對了一個帖,不停的重複臨摹,而不去動腦筋想,形成抄帖,這樣很難進步。在指導學員的章草時,劉文華老師又說,一些誇張的用筆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個性所在,像這種誇張顯得很空,不學。每一個字要熟練,先向象裡寫,再往熟練寫,再背臨,要學會過單字關,不能只抄帖。你現在要換一種方式,一個字寫五、六遍即可,照著寫兩遍,一定要往像裡寫,然後找感覺,比如背著寫,看能否記住,再進行用筆的動作訓練,從速度、虛實、比例等方面提煉著去寫,有針對性、有目的的去訓練,把每一個字都寫透它,也就是從生到熟到背到各種轉換,不斷提煉,最後放開去怎麼寫都高級。也就是說,哪怕只吃一個豆也一定要把它吃到肚子裡去,吃得東西不在於多而在於能不能發揮作用。
四、核心的東西是永遠不變的
劉文華老師在講到隸書時說,核心的東西是永遠不變的,字再怎麼寫,關鍵的部位要控制住,關鍵部位之外的誇張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間部分來決定中國方塊字,任何一個都是這樣。凡是誇張的筆畫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規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變化是哪兒來的,實際上是允許誇張的筆畫誇張程度的不同引領了風格的不同,同樣是在方塊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結構是死的,而只有細微地方的變化,這是一個原則,方塊內的不動,而決定字的風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細微變化的地方誇張的不同,這是一個基本規律。有的字為什麼老寫不好,就是內在的筆畫沒有寫好,內在的部位可以粗細不一樣,大小不一樣,但都必須擺勻它,你可以誇大或縮小比例,但必須寫勻,要求趣味和變化,必須先有這個理,掌握了這個理再去變化,比如這個“張”字,我們畫一個方塊,方塊內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變的,把“弓”和“長”的某些筆畫在方塊內部變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變成張遷或是鮮於潢了嗎,如果把‘“弓”的第二筆橫畫和第三筆的彎鉤向左誇張一些,再把“長”的橫畫和捺向右誇張舒展一些,這不就成了禮器或者是曹全了嗎,以此類推,其它字也是這個道理。因此,臨帖方法要變,觀察的方法要變,思路要變,訓練的模式也要變。
五、意臨不可或缺,要學會消化,搞創作時要活學活用。
在點評一個學生的對聯時,劉文華老師說,寫對聯字寫得這麼大,筆畫要加粗,原帖上的筆畫粗細是如此,但你把字誇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筆畫誇大了兩倍甚至不變,這不行,搞創作要活學活用,創作時要有一些調整,比如這個“畫”字,上邊輕,中間加粗,然後下邊要突出禮器碑的風格,這樣才行。你的臨帖中缺少一個意臨的過程,照著寫要往像裡寫,背著寫要往熟裡寫,然後再照著寫時往不像裡寫,雖然不像但怎麼看還都像,然後再怎麼看還都不像,在似與不似之間,比如說你兒子,外表和你不一樣,咋一看不像你,但真的不像嗎,他還必須得像你。我們在消化古人的時候,這種像與不像就不是一個表面的像與不像,而是一個精神和原則的像與不像。也就是說你缺乏一個環節,臨帖時沒去進行意臨消化,當然,這個消化也有個方法,比如說這個“膠”字,臨熟了之後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虛實、濃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寫完了,像麼,絕對不像,不像它具體的每一個筆畫,但是美感還是它,不管你如何去變,只要這裡用點去處理了,都還是它。這種不像是微觀的,像是宏觀的。藝術不是老百姓說了算,在中國歷史上藝術是貴族的產物。天天講喜歡藝術,喜歡就是會嗎,能寫幾筆就是懂嗎。因此,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沒用,照搬古人是沒腦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腦子才行。現在講科學發展觀,發展是必須的,能不能發展要看你能不能科學,科學才能發展,不科學還發展什麼,事就是這麼個理。要站在古人的基礎上去把古人的原則借鑒過來,原則、方法、標準、規律、基本技法等借鑒過來以後,你自己要做一個加工廠,要思索、研究、試驗,而科學的試驗、合理的試驗,才能是有效的試驗,這樣用在創作上才行。
六、不要把字工藝化、模式化,要恢復它的自然狀態。
在講評一幅《張遷碑》的臨作時,劉文華老師指出,要恢復它的自然狀態,張遷碑的趣味特點,一是筆沉,再一個是筆的拙樸,古人寫字不是在搞創作,他要是搞創作求趣味,東歪西斜,恐怕腦袋就沒了,官刻,給孔老夫子刻、給皇上刻,你刻得歪七斜八,腦袋不是沒了嗎。什麼叫封建,它是貴族的一種統治,傳統文化是按儒家學說走的,儒家推崇禮,說話辦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勢,幹什麼都要行個禮、講個法,那叫一種制約,封建統治就是由統治者確定的那種制約太多,而且中國書法的發展從來就沒離開過統治者的意識,所以南北朝統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門,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來人們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這都是以統治者的意識為轉移的,那麼,它追求的美是什麼美呢,不是追求怪異的美,而是端莊的、和諧的美,端莊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莊嚴、肅穆,和諧的美就是虛實輕重等書法的所有變化都在陰陽的學說當中,和諧來自陰陽的協調。所以,陰陽的協調是書法的味道,而端莊、嚴謹是正大氣象,是書法核心的東西。為什麼很多人搞書法不能成家,就是他們認為搞書法是自己的事,“我就這麼寫,只要我覺得好願意咋寫就咋寫”,其實,我在課堂上說過多次,人寫字如果寫到沒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書法是個大文化,不是你喜歡怎樣就怎樣,比如,你喜歡坐著寫,我說你要站著寫,這不是我讓你站著,而是這個字要求你站著,往規矩裡去寫。像你把張遷碑寫到這種程度,你就應追求一種自然,張遷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筆畫位置的錯落上的變化,不是筆勢上的變化,而是字形結構上的變化,是比例上的破壞和筆畫位置上的破壞,而不是筆勢上的事,曹全是筆勢上的而張遷不是。弄清這點,在寫的時候就要把這種自然狀態還原。
另外,隸書本來修飾美感就強,沒有必要再去增強這種形式美感,不然就會把字工藝化、模式化。隸書的高級程度應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強化這種形式美感,要完全變成一種自然的書寫狀態,增加用筆在紙上的平緩,在平緩的同時增加彈性,就像音樂一樣,有快慢、緩急、輕重、強弱。當今書家多是在用一種模式書寫,這最麻煩,可能一時出彩,但這種出彩三年也維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鮮於潢,碑陰變化變得越來越純樸,越來越單純,什麼是樸實,就是直來直去,就是簡單,簡單得沒想法,這種樸實咋一看沒想法,而你如果去聯想,想法可又就多了。因此,真正的藝術有兩種狀態:一種是成熟狀態,成熟狀態完全是理性的、規則的、法度的;另一種就是非理性的,藝術發展到沒成熟,有法式但不嚴謹,就像小孩走路,他還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幾步特可愛。我們現在就追求藝術的理性的、嚴謹的、規則的東西,他作為一種規範性,規定著本體的屬性,像正大、端莊、肅穆。但藝術半生不熟的勁和不加修飾這種勁,是藝術的趣味、境界、味道。兩歲的小孩做一個動作成熟嗎,不成熟,他說話,主次混亂說不清楚,但你就覺得他那個動作和說得話有味道,好玩,可愛,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氣所反映出的一種東西。我們的眼不能老盯著當代書家,而應多臨帖,從碑帖中去尋找和恢復其自然狀態,像你們高密出土的《孫仲隱碑》,雖然說規模小一些,但內容樸實以及它那可愛勁,在漢碑當中是高級的。
在談到清人的隸書時,劉文華老師又講到,清人最大的貢獻就是把碑的刻字變成了墨跡,把刻出來的字變成寫出來的字了,書寫性本身就是一種還原途徑,這是清人唯一的東西,再一個,像鄭谷口的機靈勁、陳洪授的放浪勁、鄧石如的平和勁,趙之謙的結實勁,俞曲園的溫潤勁等趣味性的東西都可學,但真正的法則還要學漢,字法還是得從漢碑中來,也就是最終的原則把握還是要學古。
七、碑陰與碑陽----趣味與法度的互補
漢碑分碑陽和碑陰,其背景知識對我們讀帖和臨帖有很大幫助,劉文華老師在講評中談到,帖上的東西你要會看,碑陽是正文,是給別人看的,碑陰則是說明,古代人刻碑永遠都是正面規範、嚴謹,而背面隨意、沒那麼多限制,對外的碑陽是規矩的,到陰面時就不講究。陰陽在歷史上永遠是兩種狀態,面南側謂之陽,面北側謂之陰,如濟陽是濟水之南,淮陰是淮水之北。碑陽面寫正文,碑陰面則是一種說明,比如誰出的錢,誰刻的字等;還一種是正文寫不下就往碑陰寫,像禮器碑,字太多連碑的側面也用上了。碑陰一般都是韻文,四字韻文,讀起來朗朗上口。同時對刻工來說也是一種體例,漢印從刀法上有兩種,一是嚴謹的,還有一種是急就的,如將軍印,臨時定的,必須馬上鑿出來,不加修飾,形成急就印。碑陽的正文講究,刻工刻得也講究,到了碑陰,寫得不講究,他刻得也不講究,寫得隨意刻得也隨意,這種講究與隨意也反映的是一種刀法。因此,要把碑陽的東西方當成規範、法度,把碑陰的奇趣當成變化的手法,研究學習碑陽時是為了取法學成規矩,其筆法的嚴謹、講究、細膩,起筆、行筆、收筆等規範度都是碑的極致,而學趣味一般學碑陰。前邊法度嚴、趣味差,死板,後邊法度差、趣味妙,兩者正好互補。碑陽的規則法度雖然死板,但他也告訴你一種變化意識,這種意識雖然不如碑陰顯得活潑、輕靈,卻可用碑陰的起收筆的狀態去改變碑陽裡的那種狀態,用後面意的東西去化前面法的死板,這不就行了嗎。而一味的誇張,一味的加粗,其實不是變化,只是讓人看到我們思路上的一種混亂和模糊。當你理解了這些,就會在臨帖時學到碑陽的嚴謹法度,規範技法,又會學到碑陰的率性個性,藝術趣味,兩者結合使作品莊重而不呆板,輕靈而不輕浮。
八、臨帖上不能出問題,創作上永遠都保持一種向上的狀態。
談到繼承與創作,劉文華老師說,臨帖就是在繼承,你如果能消化的去臨,有目的、有思想的去臨,臨完了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創作。你看咱們有點成就的那些中青年書家,為什麼三年、五年就沒了,他用功的時候,夾著尾巴做人,開始投稿的時候,甚至能找八百個人看,請教,好歹上了一次、兩次,自己成了,再投稿時也不找人看了,然後自己的習慣手法也出來了,按自己的習慣去寫,古法就少了,再寫古法更少了,習慣更多了,再寫古法基本上沒了,全剩下自己了,然後怎麼投稿也上不去了,到了明天就開始罵街了。書法界連續五年獲獎的,連續五年站在創作前頭的這樣的人相當少,基本上是三、四年就沒了,能堅持十年,創作上每次都上,這樣的人極少。二十多年以來,八十年代成名的書家留到現在創作上依然站在前列的有幾個?一巴掌也不夠;九十年代成名的書家留到現在的,你能數上十個算不錯了,為什麼?都是在臨帖上出了問題。中國歷史上的藝術家,先不說藝術大師,只要是在歷史上能留下的藝術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從出道開始一直到死在創作上永遠都是一種向上的狀態;二是他所有的創作,包括個性的張揚和他自己面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一種昇華,而不是破壞了傳統的模式;三是所有的藝術家都是有思想的,不是玩字體的,而是玩思想玩理念的。如果要成為大師,那還是要有見地的,有身份的,在書法界、藝術界始終都是最活躍的,而且是對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藝術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人物,那就是准大師,而且從一出道開始一直到老始終處在藝術發展的風頭浪尖上,他是風雲人物,引領著創作一輩子,再加上社會地位,獨到的理論,而且他的思想、理念永遠在別人前頭,像張大千、齊白石、李可染、陸嚴少、黃賓虹,哪個大師不是這樣。
因此,要用規則武裝頭腦,要用一種信念去科學的分析、科學的訓練和總結,該取的取,該捨的捨,要有目標。別人弄過的咱會了,別人沒弄過的咱永遠不去想,不行;你要弄出個別人沒弄過的,讓他老跟著你跑才行。這幾年跟著我跑的就是這樣,因為他腦子跟不上我,這並不是說我多聰明,我只不過是站在一個好的平台上,這個平台決定了你必須要往前走,必須要跑在前頭。
九、通過學習去理解法和意的東西,從而獲得一種原則
在講到對米芾的臨習時,劉文華老師從幾個字的示範上進行具體的講解:你看米芾的這個“奉”字,從方向上,第一筆稍微往上去,第二筆往下來,第三筆又往上去,這三個筆畫的運行正好是三個不同的方向,方向上互相交叉,這是筆的運動方向,那它是否就是單純的往上或者是往下呢,還不完全是,往上的同時還有點往下闔和感覺,是裹著筆的,三個筆畫都是如此,所以它把這三個運動方向裡面又增加了內在的東西,總體往上還往下,總體往下還有點往上,每一筆都較著勁,就像我拉你過來,你不得不過來但還不想過來,繃著勁,這就是由筆畫的限形產生的彈性,一種力度。前者往哪個方向行筆反映的是方向知識,而後者“繃或擰”的裹筆反映的是內在的一種勁,什麼叫作合理,一個是把筆的方向寫出來了,一是把這種勁寫出來了,彈力和勢寫出來了,也就把意寫出來了,至於長短寬窄不是主要因素。因此,這是一種技法要求,而這種技法告訴你的不僅是一種運動狀態,更是一種生命狀態,所以,我講課時經常說,要把字寫活,寫出一種生命狀態,是一種活的東西,喘氣的東西。如是,只要把這種筆勢寫出來了,怎麼寫都是米芾,為什麼,就是它用筆和習慣、用筆的手法、曲直的控制、還有這種筆勢,整個和米是一致的;而如果換一種手法,劉文華老師一邊示範一邊講,比如這個地方是誇張的,這個地方也是裹著的,這就不是米而是顏了,即便是顏,那麼它與米有沒有關係?只不過顏這種裹著筆的東西多,而米裹的東西少而已。顏的風格是圓轉筆法、篆籀筆法多於米,而米的圓轉少而且更加含蓄,他更多的是一種霹靂啪啦的折筆和切筆等,所以顏的字內含、圓潤得多,而米則是勁捷和峭拔得多,因此,藝術的風格是靠筆法決定的,就像剛才示範的這幾個字,在某一方面稍微一誇張就成了顏了,把某一方面稍微一強化就成了米了,它是一種筆勢的改變,我們應特別關注這個勢字,就能把意表達出來,也就是把它的結構原則用上,又在你筆下得到一種強化。為什麼我經常說跟我學書法是在學理法呢,不是說讓你寫得必須與它一模一樣,是讓你通過它去瞭解一些法和意的東西,然後探討什麼樣的手法、什麼樣的動作表達出來,這不就成了技法了嗎。面我們在學習真正關注的不是技法,而是關注它的理念、理法和原則,我們臨帖不是拿起筆就抄,甚至於還哼著小曲,這樣你能寫好嗎?我們所有人寫字上的差距是怎麼產生的,那就是寫得特別好的人他絕對是研究它的專家,不斷的進行研究、分析、試驗、歸納,再試驗、再總結,是在通過字形結構,包括筆勢、字勢等的研究去獲得一個原則,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臨帖,而不像有些人所謂的臨帖只是抄了一遍內容,其它的要素與帖一點關係也沒有。所以,你們現在臨帖的點不對,有時候學員感覺寫得像的時候老師不一定說好,寫得不像的時候老師不一定說不好,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好壞關鍵不在於像與不橡,而在於合不合理。
十、神采為上的關鍵——由動態的勢去把握字的生命狀態
對勢的重要性,劉文華老師從王到顏再到米的字形和用筆的變遷以及筆勢的微妙變化進行了示範,從每個字的具體筆畫,每一個筆畫的方向、勢、勁、外在的和內在的呼應連帶以及彈性、力度等到方面做了詳細的講解,同時強調,臨帖不是要你臨的多像,而是取其外在的態勢與內在的品格,技法告訴你的不僅是運動狀態,而且是一種生命狀態。對於書法,明眼人特別注重勢,也就是運動狀態的把握,民間寫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結構,而從專業上講,則不是關注其字形結構而主要是關注字勢和筆勢。勢,主要是說一種勁或架勢,一定是一種運動狀態,人有某種勁或架勢,它反映了人的某種心態,字有某種勁或架勢則反映了這個字的神采,表象反映出一種運動狀態,卻告訴你一個內心的東西,同時也就給某一筆畫或某一個字賦予了一種品格。這也就是我講課的時候經常說要把字寫活,寫出一種生命狀態,喘著氣動起來,比如米芾的這個:“勝”字,左低右高,這三個豎著的筆畫,不是直上直下,不是垂直而是斜一點,總體有種上躥的感覺,而且還帶著橫勢,只要把這個意思寫出來了,字勢掌握了,運動狀態掌握了,就可以放開寫了,怎麼寫都行,只要字勢出來了,別人一看就知道是米芾。米芾就是善於營造一種險勢,每一個筆畫都動起來,還較著勁,特別有味道。因此要通過這種字勢和筆勢的關注,去把握字的運動狀態和生命狀態,表現出特有的神采。
十一、王羲之的貢獻----給中國人用毛筆寫字提供了一個審美空間。
在講評王羲之行書的臨作時,劉文華老師講,你書寫用的毛筆筆鋒太長太硬,古人在明以前無長毫,經典的帖基本上都是在宋以前,宋以前第一無長鋒,第二無羊毫。寫王羲之,一是筆要硬,再就是寫出來要溫潤、典雅,也就是含蓄勁。王羲之的主要貢獻,是給中國人用毛筆寫字提供了一個審美空間,就是注入了一種文化氣息,也就是每一個筆畫、每一個字都帶著一種文化理念在裡面。受限制的書寫,都是一種理性的書寫,都是一種有思想的書寫,所以,王羲之的貢獻是這個而說不是他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蘭亭序》或是其他碑帖,他不是一門技術,它是一門理論。因此,學王羲之,首先要把握他的書法特徵、書法理論、書法法則,這也是所有學書法的人你都不能繞過他的原因,不管什麼情況你都要從王羲之那是走,因為你不學王羲之,最終得不到字的典雅,得不到文氣。